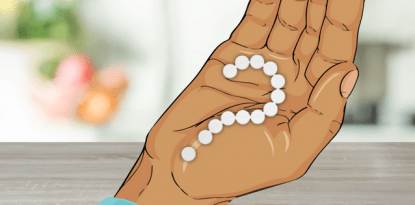“城市改变糖尿病”峰会:城市2型糖尿病的文化和社会驱动因素是什么?
作者:Emily Regier, Kelly Close
推特摘要:诺和诺德公司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城市改变糖尿病峰会”的主要要点
 我们的团队有幸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参加鼓舞人心的活动诺和诺德城市糖尿病改变峰会.首脑会议突出了联合国第一年的调查结果城市改变糖尿病计划该研究旨在研究城市2型糖尿病的主要社会和文化驱动因素。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城市,包括三分之二的糖尿病患者(超过2.5亿人)。全球有五个城市被选为该项目的第一年,分别是休斯顿、哥本哈根、上海、天津和墨西哥城,以及约翰内斯堡和温哥华加入这个项目第二年。
我们的团队有幸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参加鼓舞人心的活动诺和诺德城市糖尿病改变峰会.首脑会议突出了联合国第一年的调查结果城市改变糖尿病计划该研究旨在研究城市2型糖尿病的主要社会和文化驱动因素。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城市,包括三分之二的糖尿病患者(超过2.5亿人)。全球有五个城市被选为该项目的第一年,分别是休斯顿、哥本哈根、上海、天津和墨西哥城,以及约翰内斯堡和温哥华加入这个项目第二年。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五个城市都遵循一半原则:一半的糖尿病患者被诊断出,一半被诊断出的患者得到治疗,一半被治疗的患者达到目标,另一半达到目标的患者避免并发症。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比如哥本哈根98%的糖尿病患者接受了一些治疗(而不是50%),墨西哥近70%(而不是50%)的糖尿病患者没有达到血糖指标。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率从哥本哈根的5%到上海的略低于18%不等。
除了介绍五个参与城市的初步研究成果外,峰会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小组讨论,包括“城市糖尿病”(城市中的2型糖尿病)的主要社会和文化贡献者,以及如何利用城市作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模式。
我们的五大收获
1)城市糖尿病最大的社会风险因素是什么?
David Napier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综合了过去一年的研究结果,指出四个社会因素是众多人群中风险的关键决定因素:
金融约束:他强调,财政限制不仅包括使人们无法获得基本资源的绝对贫困,还包括限制人们积极主动和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能力的可感知的限制。
资源约束:资源限制通常与财政限制联系在一起,但更具体地定义为无法获得当地的医疗保健、药物、营养食品、锻炼或教育资源。
地理约束:这些问题包括一系列在城市环境中被放大的问题,如污染、犯罪、基础设施,甚至隔离。
时间限制:纳皮尔博士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必须优先考虑生活中的每件事。对于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来说,医疗保健往往远远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许多人已经被工作和家庭责任压得喘不过起来。
Napier博士强调,在解决糖尿病的脆弱性时,必须考虑文化和社会因素。这意味着要问这样的问题:(i)病人觉得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吗?(ii)饮食建议是否与人们的饮食传统相冲突?(iii)糖尿病是患者最大的问题吗?以及(iv)该人认为什么是正常或健康的身体类型?
2)气候变化和糖尿病?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出现了。
诺和诺德执行副总裁贾博·里斯宣布,诺和诺德将与C40城市气候领导小组建立联盟。C40成立于10年前,是为了应对G20峰会对气候变化缺乏关注的问题。自那时起,中国已发展为82个“特大城市”,占全球GDP的25%,截至2014年,共采取了8068项具体减排行动。C40执行主任马克·瓦茨先生指出,各成员城市报告说,他们30%的行动直接来自于与网络中的其他城市分享知识和最佳实践,这表明像这次峰会这样的会议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
3)同伴支持如何影响糖尿病结局?
Edwin Fisher博士讨论了同伴支持如何帮助解决糖尿病风险的社会决定因素。他强调,大多数糖尿病患者每年在医生办公室花大约6个小时(最多!),每年自己管理糖尿病的时间为8760小时。Fisher博士简洁地说:“人们需要帮助来度过这8760个小时。”同伴支持者可以特别有能力提供这种帮助,在诸如糖尿病的日常管理、与临床护理和社区资源的联系,以及可能最重要的社会和情感支持等领域提供帮助。事实上,费舍尔引用的研究表明,社会孤立和吸烟一样致命。
此外,同伴支持能够使那些医疗保健往往“难以触及”的高优先群体参与进来,这些群体包括风险特别高或临床状况较差的群体、少数民族和财政资源较少的群体。
4)我们怎样才能使健康变得轻松愉快呢?
在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小组讨论中,发言者提出了使公众健康干预措施方便和有趣的重要性。正如Helle Søholt女士(Gehl Architects的首席执行官)所指出的,56%的哥本哈根人骑自行车上班是因为环境迫使他们这样做——“这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这是最快、最简单的出行方式。”美国卫生部长Vivek Murthy博士最近在2015年TEDMED会议上谈到了“幸福”作为一个公共健康焦点的相关话题,他指出,幸福只能改善情感健康,但也能改善身体健康。
(5)走向集体效应。
城市变化中的糖尿病突出了当今糖尿病背后挑战的复杂性。除了糖尿病的生物成分外,还有无数的因素会导致糖尿病的风险,这使得一旦糖尿病发生,管理糖尿病变得越来越困难。首脑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集体影响"的概念,即侧重于跨部门合作(即食品工业与城市规划者合作与医院等)以解决糖尿病预防等复杂问题的解决办法。正如波士顿FSG的John Kania先生所说,“如果你想改变系统,你必须让系统进入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