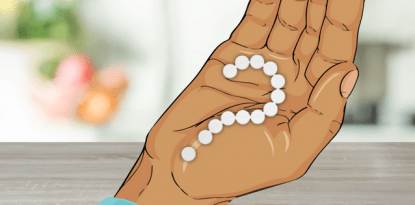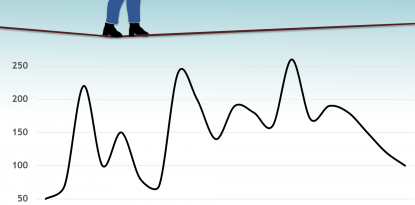夏令营:碳水化合物计数,灵感和一个特殊的火炬

詹姆斯·赫希(James s. hirsch)著
我不太明白火炬的意思。
8月,我们全家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牛津市的克拉拉·巴顿家庭夏令营。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这个夏令营是为患有糖尿病的女孩准备的。乔斯林男孩训练营离这里只有10分钟的车程,但在8月份的5天里,在200英亩的林地、徒步旅行小径和操场上,克拉拉巴顿是整个家庭共享床铺、数碳水化合物、开怀大笑和擦干眼泪的地方。
今年夏天大约有30个家庭参加,每个家庭通常都有一个糖尿病儿童,这些孩子要么年龄太小,要么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参加糖尿病露营。(许多兄弟姐妹也参加了。)我们的儿子,加勒特,三年前被确诊,现在六岁了,所以明年,他就能去乔斯林夏令营了。但就像我说的,我不确定火炬的事。营地里有一家礼品店,加勒特买了一条带镍大小的锡制饰品的项链。一边写着:“巴顿1932”,这是营地成立之年的美好回忆。另一边刻着一个火炬,上面有五颗小星星像烟雾一样翻腾着。
护士:“我叫多萝西,但大家都叫我泡泡。”
谢丽尔(我的妻子):“我可以叫你多萝西吗?”
谢丽尔是一个有爱心的女人,但她不会与任何名字让人联想到肥皂水的人建立亲密关系
火炬是否象征着难民营试图开辟一条更好的道路以获得更好的照顾?还是成为糖尿病儿童的一盏明灯?还是向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表明了我们的力量和活力?或者说,这个燃烧的图标是为了连接在这个营地上的一代又一代的患者,他们传递了同情、友谊和爱的火炬?
我猜加勒特只是觉得火很凉。
不管怎样,我们都不用担心加勒特会不会合得来。他和两个精力充沛的四岁和六岁的兄弟很快成了朋友,他们住在我们的小屋里。第一天下午,四岁的儿子问加勒特:“你愿意做我最好的朋友吗?”——他们很快就开始计划夏令营结束后的玩耍约会。这很好,除了我们住在波士顿地区;他们在洛杉矶。
每个客舱都分配了一名护士,当这些家庭到达时,护士为他们登记。我们的护士,一个矮胖的女人,一头短短的金发,从德克萨斯州大老远赶来。
护士:“我的名字叫多萝西,但每个人都叫我泡泡。”谢丽尔(我的妻子):“我能叫你多萝西吗?”谢丽尔是一个有爱心的女人,但她不会和任何名字让人想起肥皂水的人建立亲密关系。加勒特没有这样的保留。第一天结束时,他在小屋里跑来跑去,尖叫着,“我要吹泡泡!我要吹泡泡!”
营地在糖尿病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美国糖尿病协会(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现在认可了其中的122种,我不知道还有哪一种儿童疾病是这些“林中医院”——它们最初被称为“林中医院”——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虽然第一个阵营的创始人艾略特·乔斯林博士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但我怀疑就连他也预见到他将留下什么。
1922年胰岛素被发现后,乔斯林意识到把糖尿病儿童聚集在一个营地的价值,在那里他们既可以玩得开心,也可以学习糖尿病自我管理的基础知识。当乔斯林在波士顿训练时,他在西部55英里的牛津长大,他的同名营地于1927年在附近建立。除了医务人员和顾问,它还有一个化学家的实验室,测试营员的尿液样本中的糖。1932年,乔斯林加入了普世主义妇女组织,在已故的克拉拉·巴顿出生的地方为患有糖尿病的女孩建立了一个营地。巴顿本人就是一名普世主义者,她是一名具有开创精神的护士和教师,人们最难忘的是她创立了美国红十字会。
人们只能想象几十年前那些糖尿病露营者的经历。如今,一个新诊断出孩子的家庭可以通过互联网立即与数百个(如果不是数千个)有同样经历的家庭联系起来。聊天室,支持小组,博客,我敢说,甚至谩骂-创建一个真正的社区。
但20年前,更不用说75年前,一个糖尿病儿童更有可能感到孤立、疏远和孤独。除了在夏令营,所有让孩子感觉不一样的事情突然变成了常态。事实上,我不需要想象很久以前那些孩子的经历,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在高中和大学时,我是密苏里州一个糖尿病夏令营的辅导员。在一个令人心酸但很典型的故事中,一位辅导员同事告诉我,她是如何很晚才到营地的,当她开车过来时,她从一座小山上往下看,看到整个行动——100多个孩子聚集在一起,有说有笑,继续进行。一张长桌上放着胰岛素瓶、注射器和酒精棉签;每个人都准备好了他们的剂量和注射。一切都是这样……正常的。
我的朋友告诉我,在她的一生中,她第一次不再是局外人了。所以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她哭了。正如我今年夏天在克拉拉·巴顿发现的那样,自那以后,夏令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糖尿病一样。当我还是一名顾问时,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注射次数(两次)和基本相同的胰岛素(礼来公司的NPH和普通胰岛素),而我们这些准备拯救世界的顾问会拿着我们的剪贴簿四处走动,拿着写有尿液检测号码的医疗单和一个装有糖包的塑料袋。
在克拉拉·巴顿,治疗方法和孩子们一样不同,孩子们总共有四种不同类型的胰岛素泵,至少每天注射那么多,天知道有多少种饮食。咨询师们现在正在走药剂师,拉着血糖仪、葡萄糖条、酒精拭子、小柳叶刀和葡萄糖标签。
家庭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人250美元,外加50美元的注册费。设施再好不过了,有现代化的小木屋、餐厅、游泳池、整洁的运动场、谷仓般的剧院、会议室和办公室。白天,孩子们有自己的活动——运动、游泳、艺术和手工艺、健康和饮食指导——甚至兄弟姐妹也有专门的会议讨论他们有糖尿病兄弟姐妹;加勒特的姐姐阿曼达也是出席者之一。家长们也进行了间歇治疗。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用。例如,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工作者,他允许我们发泄我们的挫折感,并鼓励我们在家里建立一个支持网络。
还有一次,我们上瑜伽课。我以为他们说的是酸奶,所以我提前到了。那个女人一直让我放松,但我满脑子都是我的电子邮件。灾难。
和这么多的人在一起,住在这么近的地方——我们的小木屋里有15个人,包括3个顾问——让我们意识到其他家庭是多么的聪明和机智。例如,有一天午夜,在我们的床上,一个在打气瓶上的女孩血糖约为80毫升/分升——这在睡觉时有点危险。我以为她的父母会给她一份零食。相反,他们暂停了她的基础胰岛素一个小时,在不影响她睡眠的情况下,略微提高了她的血糖。辉煌。现在是为了加勒特
有些想法不太实际。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有糖尿病女儿的妇女向我们讲述了她管理家庭的非常有条理的方法。她用维可牢尼龙粘扣在厨房里的每一种食物上都贴上了碳水化合物计数,这对于我们这些几乎没有时间把食物收起来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想法,更不用说记录碳水化合物了。但我们认为维可牢尼龙搭扣的女人很有活力。
营地负责人要求家长们留在营地,但我得说,在营地里,五天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到了第三天,我和另一位父亲,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油漆工,密谋越狱去唐恩都乐喝咖啡。
一些发言者试图传达这些年来糖尿病护理有了多大的改善,但家长们在描述他们自己的恐惧和心碎时,清楚地表明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一位母亲说,她的孩子因为糖尿病被私立学校拒之门外。另一位母亲说,她的女儿曾拨打911,要求换一个妈妈,因为她的妈妈“给她打了太多针”。一位父亲回忆说,他的小儿子问他:“如果你不在这里,谁来照顾我?”
另一位母亲说,她的儿子将帮助经营一个柠檬水摊,这样他就可以找到糖尿病的“诅咒”,这样他就可以吃更多的碳水化合物。
但鼓励来自于糖尿病咨询师,其中一些人在某晚的一次突发会议上对我们说。他们谈到了自己与父母、学校的斗争,以及作为一个年轻人和糖尿病患者之间的平衡。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他们都讨论了夏令营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位顾问说,这是“裤裆里的一脚踢”,迫使她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夏令营将你推向自己的极限——“冒险项目”包括徒步攀登海拔6200英尺的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并建立持久的友谊。他们也给日常斗争投下了完全不同的光。一名咨询师指出,camp最棒的地方在于“这里根本不存在糖尿病。”
.jpg)
另一位咨询师说:“我喜欢糖尿病,因为它成就了我。如果真有解药,我也不想要。”在大学里,她想主修“娱乐服务,这样我就可以永远来夏令营了。”
尽管这些年来这些阵营可能发生了变化,但基本要素仍然是一样的。这是关于孩子们快乐的故事——每天早上升国旗,白天玩游戏,晚上在篝火旁唱歌——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就像他们一样。一个男孩告诉他的母亲,他喜欢夏令营,因为这是第一次,他不必在胰岛素泵上脱下衬衫。
对加勒特来说,最精彩的是尝试“滑索”,你在腰上系上安全带,爬到50英尺高的树上,站在一个平台上,把自己绑在两棵树之间的缆绳上,跳跃,并在滑索时挂在上面。你不可能真的伤到自己,因为你被绑在一根绳子上,这根绳子是由地面上的顾问拉着的。尽管如此,要爬上这棵树还是很困难的(你要把你的手和脚放在钉在树干上的金属杆上),把自己拉到平台上也不容易,最终需要真正的信心飞跃。
像加勒特这样的小孩能做到吗?他戴上橙色头盔,扣上安全带,开始向树上爬去,每一步都有条不紊但自信满满。他爬上平台,连接电缆,在地面上的伙伴们为他加油的情况下,他跳得尽可能远。
当然,火炬象征着一切——拿着它的人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疾病的开拓者,他们是激励和勇气的灯塔,他们是将希望之火传递给后代的无名儿童。
当加勒特沿着拉链线航行时,我知道这一点。为了炫耀,他把自己47磅重的身体倒过来,让脚趾指向天空。他很快就回到了地面上,神采奕奕,无所畏惧,仍然带着手电筒,前往克拉拉·巴顿营地的树林,寻找一条奇妙的新路。